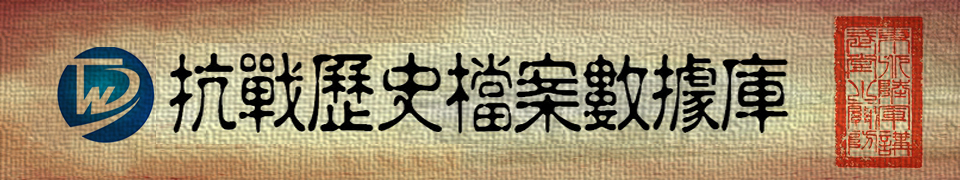东北讲武堂教职员名录
东北讲武堂的黄埔籍教官
2021-8-16 21:32| 发布者: admin| 查看: 3758| 评论: 0|原作者: admin
东北讲武堂前身是东三省讲武堂,成立于1906年秋,1908年10月改名为东北陆军讲武堂,设立于奉天(今沈阳市)小东边门外。1919年3月再度改名为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是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事集团自办的第一所军事学校。从1919年5月起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止,东北讲武堂共培训学生8900余名,加上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前期培训的学员,总计约11000多名学员与教官。从培养初级军事人才总量计算,与稍早期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比较毫不逊色。 东北讲武堂在教学内容、规模、质量与影响诸方面,与北京陆军大学、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云南讲武堂同时齐名,同为我国军事教育现代化的著名军校之一,东北讲武堂还因设立与办学早于黄埔军校,闻名于国内军界先于黄埔军校。东北军(奉军)作为近现代军事历史上曾经强盛一时的军事集团,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我国北方有过重要历史影响和作用,而东北讲武堂则是培养孕育这一军事集团将帅首脑的军官摇篮。无疑是我国第一批正规军事院校和清末民初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陆军训练中心,它的诞生与发展,堪称近代以来东北正规军事教育之开端及里程碑。 东北讲武堂生真正与黄埔军校发生联系,是在1928年所谓第二期北伐战争以后。学员基数较大的东北讲武堂生,东北军正规部队吸纳与容量有限,除北方派系军队吸收部分外,一部分后期毕业学员流向了黄埔军校。鉴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各分校尚无公开出版校史与同学录,目前史载与黄埔军校有关联的仅搜索到54人。这份名单中,最著名的是少帅张学良,1928年12月东北易帜不久,就被聘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1935年4月2日获任除蒋介石以外的最高级别一级上将,与同时获任的另七名相比是最年轻的,这时没满34岁的张学良整整比其中次年弱的一级上将小十岁。除少帅之外,东北讲武堂生在任教官名单中,没有很有名的人物,检索起来只有获任少将的张廉春(1947.11任)和李铁醒(1948.9任),其余还有7名获任上校军官。 与前完全不同的是,东北讲武堂生在后三个时期才有任教官。第二时期有15名,第三时期有24人,第四时期上升到33人。三个时期教官分布情况较为合理,符合东北讲武堂后来之命运和境况,紧随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自行消亡,接着西安事变后少帅被长期囚禁,它的学生在黄埔军校也难得重用。 东北讲武堂生任黄埔军校教官一览表(54名) 丁叔颖(1902-?)辽宁沈阳人,别号月新。东北讲武堂第七期炮科,南京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二期毕业。历任第五十一军炮兵团排长,连长,军政部重炮旅连长,营长,中央炮兵学校中校教官,成都中央军校第二总队上校兵器教官。抗战胜利后,任国民革命军徐州绥靖公署少将炮兵主任。1946年7月退役。 于敬三(1904-)辽宁辽阳人,南京中央军校战术教官,后任成都中央军校上校高级战术教官。 毛镜仁(1892--1974)陆军少将。字静如,浙江黄岩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3期炮科、陆军大学特别班第2期毕业。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事厅中校参谋,1928年10月任参谋本部上校科长,1937年8月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参谋本部少将高参,1938年1月任军令部第1厅少将处长,12月因病辞职回乡,1944年2月任浙江省台州专员公署护航委员会办公厅主任,1945年11月任黄岩县绥靖委员会常委,1947年4月叙任陆军少将,1948年任黄岩县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常委,1949年5月参与和平解放黄岩工作。后任浙江省黄岩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常委,黄岩县卫生工作者协会副会长,黄岩县政协常委。1974年7月病逝。 王汉儒(1910-) 字寒如,河北唐县人,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二期、东北讲武堂第八期、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二二期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中央军校办公厅总务处上校副处长、少将代理处长。 王寿贵 河北天津 驻豫军训团少校队长 刘文魁 河北蠡县 驻豫军训团少校教官 姜明文 辽宁海城 崔国英,开原人,东北讲武堂毕业,黄埔军上校筑城教官。曾率军校教官起义。 1923年12月,崔国英考入东北讲武堂工科第五期,1925年9月毕业。在1928年-1937年间,辽宁人张学良、秦 华、王多年、于国汉、崔国英、郑殿起、宁绪声、李昆山等在黄埔军校任教。崔国英是开原人在黄埔军校任教的少数教官之一。 黄埔军校任教 黄埔军校在1949年以前,按照时序和校址可以分为广州、南京和成都三个时期。成都校期因校址时间最长,毕业人数最多,在历史上留下重重一笔。新都宝光寺是黄埔军校成都校期的北部军营。 1938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中正委员长的陆军军官学校迁到成都,校本部一直设在城北北较场,第23期时为该期二总队驻地。军校通常保持两期学生3个总队约4000人,加上警卫团1200人和校部的官兵,全校共有师生、官兵约6000人,相当于一个加强旅,这便是国民党中央系统在川西地区唯一的主力部队了。黄埔军校在成都共计办了10期(从14期至23期),毕业学生31万5千余人。 这个时期,还委托各兵科学校及有关机构,代训学生1万5千余人。驻扎在新都县北门外“宝光寺”内的新都军训班共有两期(22期和23期),当年的宝光寺占地170亩,教官和学员主要驻扎在罗汉堂、极乐堂、云水堂、禅堂、戒堂等地,以寺内的紫霞山、楠木林和寺外的川陕公路作为战地训练场地,还把宝光寺的照壁临街面改造为抗战宣传栏。接收的学员来自东北、西安、贵阳、北平、成都等考区,每期编为10个中队,分属3个大队,主要进行入伍生训练,主要科目有“步兵操典”、“陆军礼节”、 “阵中勤务令”等,简称典、范、令。首先练射击技术,从“三角瞄准”到“实弹射击”一气呵成。其间着重野外教练,“地形地物”的利用,“掩蔽自己,发扬火力消灭敌人”等,一直训练到排的攻击和防守。先学射击是为了“应变”,其他科目则并列进行。“兵器课”专门讲解步兵武器结构和性能。先是图解教学,接着是实地操作,蒙上眼睛拆装轻重机枪。 外打进式教育 所谓“外打进式教育”是一种教学方法,据说是从日本和德国学来的,即实行强制性教育。凡是应学的必须学会,不许做就绝对不能做,不讲说服教育,违犯了就处罚(包括体罚)。例如:规定不管怎么冷,也不许把手抄在袖筒里和揣进裤兜中。有个同学违犯了,区队长命令他从河沟里打一盆冷水来,把手泡进去,足足泡了两个小时。按军校规定,本来不准体罚学生,但区队长们无视这类规定,搞了很多“变相体罚”。最厉害的要算“罚卧倒”了:有个同学被罚做一百个卧倒,结果膝盖和胳膊肘摔得鲜血淋漓,军服也破了,面如土色,站都站不住了,还得立正敬礼。不仅每天都可见到变相体罚现象,而且有时竟是直接体罚(打)。听说要搞“夜间紧急集合”,学生们吓得不敢脱衣服睡觉。值星官来检查,命令必须脱衣服睡。他一走,学生们又穿上衣服等着。可是,一连三夜过去了,也没紧急集合,大家都有点松弛了。不料到第四天夜里,大家脱衣熟睡时,号声响了!大家飞快披挂,全副武装到大操场紧急集合,由总队值星官指挥,跑步出发。顺川陕公路经张公墓往返约跑5公里。回到大操场进行检查,结果漏洞百出,不少学生背包散了,裹腿开了,千奇百怪。总队值星官大发脾气,凡着装有毛病的学生,都分别轻重受到处分。从此后,加强了夜间训练,包括:“口令传递”、“方向识别”、“点火”、“夜间武器故障排除”等,训练最多的是“夜间着装”。各项夜间训练科目,若是不合规定,都要受严厉处分。 二训班 1947年初冬,原陆军军官学校西安督训处,在21期学生毕业后,就没有了正期军校学生的训练任务,于是该处又奉令改为“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军官训练班”(以下简称二训班)。二训班的任务是,调训胡宗南部及西北其它部队的连、排级行伍军官,以及“青年军”中的军士班长,性质跟前第七分校所属军官大队、军官总队是一样的。训练时间很短,每期大约八个月,从1947年底至1949年春,先后办了第15和第16两期,共约三千余人。学员结业后,按规定一律返回原部队。 二训班组织机构,较督训处又有缩小,人员也较少。上校军事教官有崔国英、宁其骏、任荣甫、杜世桢、袁嗣枚、周弼、李荫清,孙康济、韩桂森、常士华、倪鼎芬、赵继图、王其昌、林立斌、黄为、毋振之、杨正黄、彭国杰、齐尚贤、张翕汉、冯超、张峻岳、丁叔颖、王刚、韩慧伯、贾长令、郑搏九、翟庆善、李振海、王斌、王为汉、汪俊德、毛镜仁、韩凤琦、丁恩麟、刘锐、赵英扬、岳俊才、戚崇仁、刘胄甲、罗涤生、赵符曾、董万兴等人。 二训班第15期共有四个学员大队,经过短期训练,于1948年夏末结业。1949年元月,迫于战争形势,对已调集来的第16期学贸各大队,不得不由副主任陈延生带领首批迁往陕南勉县,当时班部各组的大部分人员及其眷属也一道前往。1949年4月,班主任刘钊铭及留驻王曲的官佐士兵最后到达。 1949年4月,二训班第16期学员在勉县结业,当时是由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关麟徵从成都前来主持典礼的。这期学员回原部队不久,西安已经解放。其时国民党部队败乱不堪,调动颓繁,疲于奔命,二训班根本没有办法再调训学员,训练任务不能不自告结束。二训班的官佐都是胡宗南的人员,陆军军官学校极不欢迎,于是脱离了军校的建制。是年7月间,又改编为“西安绥靖公署干部训练团军官训练班”,实际上成了一个养闲单位。 不久,班主任刘钊铭调回57军,以该军副军长兼215师师长,军训班即交由副主任陈延生负责。这期间,经刘、陈商妥,将原二训班勉县仓库所存物资,悉交215师使用,崔寅光负责办理拨交手续。 二训班起义 1949年10月,军训班迁往四川新都县,住在县北门外“宝光寺”内。此前,副主任陈延生已避匿成都,这时其他负责人也四散逃逸,军训班一时形成散乱状态,人心惶惶,不可终日。11月,胡宗南部败退四川,解放军贺龙、周士第、王维周统率第一野战军进军四川,汉中失守,江岫、绵阳告急,军校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在严竣的现实面前,大家感到国民党军队的彻底失败已成定局,中国大陆解放指日可待,极切盼望早日获得解放。接着,在国民党军队不断起义投诚的启迪和促动下,军训班当时所有人员就公推崔国英(开原人,东北讲武堂毕业、上校筑城教官)、任荣甫(山东人,东北讲武堂毕业,上校重兵器主任教官)和袁嗣枚(江西临川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上校工兵主任教官)三人为代表,与解放军接头联系。没多久,崔国英、任荣甫和袁嗣枚便率领全体官兵,以原二训班的名义在新都宣布起义,大家从此走上了光明大道。 1950年元月,成都军管会派解放军十八兵团随营学校的王松林同志为军代表到新都接管,所有起义人员均被编入随营学校,分校官队和尉官队两队,仍住“宝光寺”学习。 6月,对起义人员开始进行安置和处理,有少数人留在解放军参加工作。9月确定尉级先复员。其余校级人员到1951年也陆续复员完毕。 任荣甫(山东人,东北讲武堂毕业,上校重兵器主任教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