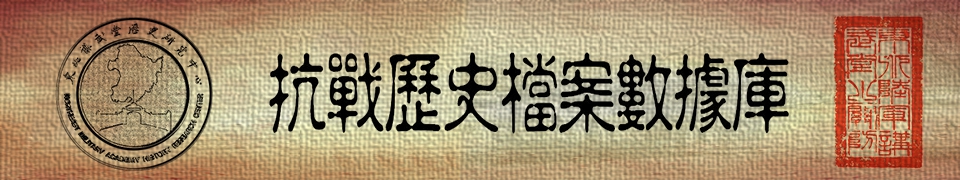918事变
您现在的位置: >>
918事变 >>
918事变
忆“九·一八”事变前后战斗岁月片段
2021-8-19 15:46| 发布者: admin| 查看: 2175| 评论: 0|原作者: 宋黎|来自: 沈阳市政协文史资料
灾难深重的旧中国,长期以来处在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两种基本矛盾之中。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一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以后,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就在这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剧烈变动的年代里,我走上了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道路。 一、从读书到救国 我是吉林省梨树县人。幼年因家中受地主欺压,幻想读点书以“支撑门面”。小学毕业后,一九二六年秋季,考入西丰县立中学。这个时期,中国以及东北的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一九二五年发生了“五卅”运动:一九二七年五月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在东北临江设领事事件,一九二八年五月,发生了中日东北铁路五路交涉案件。自从日本侵略势力深入东北,东北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即风起云涌。当时,我所在的西丰中学,反日情绪亦很高涨。正是在这个爱国主义浪潮的推动下,使我由开始抱着读书以支撑门面的幼稚想法,走上了从事抗日救亡的民族解放道路。张金辉和我等人组织同学冲出校门,到远离县城四、五十里的农村走乡串户,向农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说明事实真相,动员老百姓奋起反日。我们的爱国反日行动,激怒了日本领事馆的官员。他们利用外交手段,向中国地方政府提出抗议。西丰县政府竟勒令追查,而校长则俯首听命。反日何罪为什么追查同学们忍无可忍,遂于一九二八年秋举行了罢课、请愿活动,决心搬掉校长这块绊脚石。那时我才十七岁,勇而少谋,一怒之下,跟三、四个同学到沈阳去教育厅申诉。天真地以为这个“尚方宝剑”能够支持我们,可惜连门都没进去,反而惊动了东北地方当局。得知我们那里闹学潮,于是便派一个姓高的督学前往“查办”。这个高督学到西丰中学本想坐镇“平息学潮”。但由于罢课后尚未离校的同学都回家了,高督学无奈只好召见了学生代表。当时,我是学生代表的头。我们五、六个代表理直气壮地去见他。很有意思,娃娃们与督学大人斗起来了。他先是叫我们学生复课,我们坚持不复课。最后高督学“图穷匕见”,他大笔一挥给七、八十个学生施以“墨刑”――开除;还指令我们十几个带头“闹学潮”的,即使写“悔过书”,也不准复学。当然这其中包括我和张金辉。口蜜腹剑的高督学既对学生大施淫威,但他也怕惹翻了学生滋生意外。于是在宣布开除学生的大会上,他指名道姓地说:“宋黎,你很有才气,很能干,但不准你在西丰中学念书了,不过学校可以帮助你到其他中学读书……。”其实,高督学只是说说而已,倒是救史地的王老师真心实意地关心我们的前途,在他的热心帮助下,我们才得以到沈阳育才中学补习功课半年。这个学校是东北大学的几个学生办起来的。我们被开除又不准复学的几名同学都进了这个学校。一九二九年秋天,我和张金辉考入东北大学法预科。报考时我没有高中毕业文凭,由同学们给我造个假的。就这样得以在东大法律预科又读了二年书。在东北大学,我与张金辉、张希尧、主牺忱等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经常和东大附中的车向忱老师在一起议论,认为应该通过各种形式向中国人民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于是,我们便参加了车向枕老师组织的“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利用星期日和寒暑假期间,去向工人、学生、士兵进行反日宣传,开展抵制日货、禁止毒品等活动。一次,我们在小河沿体育场召开了烧毁日本人贩卖的毒品海洛因、大烟土的群众大会。我们还串联同学发动大、中学生和中、小学教师到学校、商店、剧场、茶馆、福音堂、街道、东北军驻地,贴标语、讲演、谈心,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以及推销国货、查禁毒品,广泛开展反日活动。我们的活动阵地是在本天基督教青年会的地下室。阎宝航是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他对我们的活动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不但借给活动场所,还担负一部分活动经费。为了提倡国货、抵制日货,我们在沈阳中街广生行百货商店隔壁开了个“大众国货商店”,销售文具、纸张、瓷器、棉纱、布匹等国货。日本侵略者对我们的举动,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他们吹着洋号,打着洋鼓,用大汽车拉着东洋货招摇“你的要不要”只要说声要,就送给过市,见到国人就问:你一件衬衣。遗憾的是,我们的铺子小,资本少,卖货不要钱不行,自然竞争不过他们。尽管这样,我们靠人民群众一片赤诚的爱国心,还是坚持下来了。我们有时还到北大营驻军王以哲第七旅宣传反日:有时他们也主动请我们去演讲,讲爱国、讲反日、讲抵制日货。这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嫉视。他们由公安局出面,禁止我们的反日活动。但是,我们的反日宣传活动,仍然一直持续到“九·一八”事变。 二、“九·一八”炮声下的惨象 “九·一八”事变前两个月,沈阳地区日本关东军就不断进行演习、示威。沈阳城的火药味已经很浓。在东北又相继发生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以及日本帝国主义者大肆则嚣“对华强硬”、“武力交涉”等等,已令人感到箭在弦上,颇有一触即发之势。我们听驻守沈阳的第七旅王以哲的部下透露,日本把大批关东军调来沈阳,日本铁路守备队秘密向苏家屯、沈阳一带集结。“九·一八”事变前几天,数十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关东军,在北大营一带连续进行实战演习。有一次,日本军的挑衅活动甚至贴近北大营的围墙。九月十七日,两名日本警察竞在光天化日之下,横冲直撞的闯进驻在北大营的独立步兵第七旅司令部,将电线切断,虽被旅守卫队强行阻止未酿成事件,但却可以看出敌人的嚣张气焰巳达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果不其然,日本帝国主义蓄谋的“九·一八”事变终于爆发了。“九·一八”事变那天,是星期六。晚上东北大学学生会组织同学们看电影,为武汉赈灾募捐。正在上演时,忽闻炮声隆隆,炮弹从房顶呼啸而过:接着北大营附近枪声四起。同学们大惊。我们遂向同学们说明这是日军在向北大营进攻,并号召同学们之即组织护校队,维护学校秩序和安全。第二天一早,我跟“国民常识促进会”的张金辉、王忱等同学进城了解一下情况。我是化妆成工人打扮。真是一夜之间,沧桑巨变往日喧嚣的沈阳城,现在噤若寒蝉家家关门锁户,路上行人寥。胡同皆是趾高气扬、列队行进的日本大兵和摇头晃脑的日本浪人。一进大西门,首先映入我眼帘的就是横曝街头的几具被日本楼人杀害的中国人尸体,惨不忍睹!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奔往钟“广生行”隔壁的“大众国货商店”。该店已被日军查封,车向忱题写的匾额和窗户上都留有被日本兵用刺刀截的一个个窟窿;国货商店商品被扔得满地皆是。我立即走开,再向大南门里的“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所在地走去。只见青年会大楼已被日军包围,一群日本兵正在挂军用电线,周围还有些便衣在转来转去。我没再前行,默然地折向皇姑屯。只见皇姑屯车站的铁路上停着一辆辆满载大炮的车箱。这些重武器是东北军准备运往关内打内战的,而今已落到日本侵略者手中,将用它来屠杀中国人民。铁路两旁,横一个竖一个地躺着身中日本侵略者枪弹的中国同胞!我穿过桥洞,猛然看到东北大学工厂的大门前守卫着几个日本浪人。看样子工厂已被敌人占领。我愤懑已极,旋即回到学校。心我刚迈进东北大学的校门便听说,南满中学堂的日本校长来看过东大校舍,还假惺惺地安抚东大同学不要惊慌。实际是日本人要占领东北大学。东大学生这时人心健惶,纷纷转移。我和张金辉等五、六十名同学跑到北陵三台子小学校,睡在讲台和书桌上。此时正值深秋时节,寒露生凉,秋风萧瑟。夜里既冷又饿,更是气愤。不过此时此刻我们是身冷心热,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翌日清晨,我们又回到东北大学。这时间学们已经星散,校园空荡荡,我们的心沉甸甸!都为敌人没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沈阳城而愤恨难平。张金辉、张希尧和我一起研究,都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不能坐视国土沦丧。我们要大声疾呼,进行抗敌复土的宣传,掀起救亡运动,阻止东北军继续进关打内战,动员在关里的东北军调转枪口对日作战。说干就干,我们三人一起从皇姑电车站上火车,向关内进发。车厢里拥挤不堪,连过道都站满了背井离乡、拖儿带女四处逃难的无辜百姓。一路上我们不时地看到全副武装的东北军和兵车仍在向关里进发。我们坐的是货车,因发生燃轴,车厢被甩摔。当我们到达锦州下车后,即向东北军独立步兵三旅张萬久的部下进行了慷慨激昂的宣传,恳请他们把枪口对准日本侵略者。很多爱国的官兵深受感动,他们表示愿意抗敌复土。但又说,他们是身不由己,不得不服从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就在此时,这位三旅旅长张禹久,正在大办婚事,娶第三房姨太太。不少妖艳的女人,奇装的男人,成群结队,吵吵嚷嚷去赴宴。国难当头,这些持枪的卫士,却在文恬武嬉,花天酒地,寻欢作乐。见此丧失民族气节的地方官吏和军官如此的腐败和昏庸,实在令人痛心。 三、打回东北 组织群众武装抗日”我们三个一贫如洗的学生到了北平,在奉天会馆落脚后,便起早贪黑,四处奔走疾呼,宣传抗日,收复失地。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敢于冒然侵略我东北三省,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东北边防要地已经空虚。一九三○年四月,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发动了对蒋介石的“中原大战”。蒋介石巧施手段,一面分化瓦解◎、冯;一面极力笼络在东北举足轻重尚未参战的张学良。先是蒋介石为张学良大庆他的三十寿辰,继之委以重任。南京政府于一九三○年六月二十一日,特任张学良为陆海空三军副司令,派人将特任委任状送到沈阳,并劝张学良出兵进关参战。两个月后,张学良在东北军的一次高级会议上曾说:“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伺已久,如欲抵制外侮,必须国内统一。我自一九二六年即主张停止国内战争,……”不久,张学良即于同年九月十八日发表了拥护“中央”的“巧电”,随即挥军关内,把几十万装备优良、能征善早日促成统战的东北国防军派去帮助蒋介石打阎、冯。东北的“看家兵”几近被调光;张学良自己也进驻北平,指挥作战。留驻东北的多是战斗力和装备比较差的省防军。日本侵略者正是利用这个可乘之机,于东北军进关整整一年之后的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开始武力侵占东北的。认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能够如此顺利地占领东北,其关键在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前一个月零两天,即八月十六日,蒋介石给张学良下达了“无论日本军队怎样导衅,我方也决不抵抗,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严令。张学良向驻扎在东北的军队高级将领作了传达,并通知“一体遵照执行”。驻守沈阳的独立步兵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执行了这个命令。尽管广大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想抵抗,但“军令难违”。虽然日军进攻时也曾违令还击,不过这种自卫性的“不抵抗的抵抗”,终归左右不了大局。所以日军不到一天工夫就全部占领了沈阳城;四个多月就鲸吞了东三省。.在北平的日子里,耳闻目睹,使我们茅塞顿开,看清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已经和即将给中国人民带来多么深重的灾难。我们为保卫祖而沸脾的热血和抗日理想,因撞到执政者不抵抗的政策而碰得粉碎。严酷的现实使我们清醒了。当年我们曾寄希望于东大爱国教授刘复主张的“飞潜政策”一一即多制造飞机、潜艇,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樱略的好办法。现在摆在眼前的现实是:面对日本的武装侵略,我们却有枪不放,有炮不发,飞潜救国计划,岂非更属纸上谈兵。蒋介石卖国,张学良按兵不动,怎么办?只有靠亡省失家的东北人民,自己拿起武器抗日救亡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罪恶行径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敢策,激起了全国人民强烈的民族义愤,特别是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中国共产党,立即表明了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态度。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联合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宣言,提出:“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的号召。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怒潮席卷全国。被日军侵略铁蹄膝璜的东北人民更是不甘心做亡国奴,愤然而起,同敌人浴血奋战。以马占山、邢占清、李杜、邓铁梅、唐聚五、苏炳文等为首的东北军旧部:以黄显声为首的公安总队、警察大队;以及许多工人、农民、学生和地方民团、保安队、绿林好汉等纷纷组织抗日义勇军,打击日本侵略者。一批流亡关内的东北人,为了“打回老家收复失地”,也纷纷组织起来。在张学良暗中支持下,阎宝航、高崇民等发起,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七日正式成立了“东北人民抗日救国会”(会址设在北平旧刑部街奉天会馆内),支持和接济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我和张希尧、王牺忱以及车向忱老师都参加了救国会。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流亡关内进行抗日复土斗争的东北同胞陆续出关,回东北参加抗日义勇军武装抗日。于是,我们决定“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的成员,除张希尧留北平从事抗日活动外,其他都回东北老家参加到抗日义勇军的行列中去。为了联络马占山、李杜、邢古清等旧东北军策动辽东抗日救国自卫军唐聚五、邓铁梅等部援助沈阳、辽西的义勇军,救国会派少数人,带着张学良用黄绫子写给马占山、邢占清等人的委任状,潜回东北工作。一九三一年底,车向忱老师和我,还有一个姓李的同学(名字记不住了),从天津塘沽乘日本“天潮号”轮船出关宣传抗日,组织抗日义勇军。为了防止意外,行前我们详细研究了潜回东北的方式、方法、路线。车向枕老师化装成药房先:生,我们俩扮装他的徒弟,从天津到大连,安全地通过了大连口本水上警察公署的严格检查。为了争取时间多做宣传、组织工作,我们席不暇暖,便踏上征途,从大连乘车出发,先后去皮口、庄河、安东、宽甸、桓仁、通化、辽源、西丰、四平、哈尔滨、齐齐哈尔、昂昂溪、洮南等地,向知识分子、农民群众和东北军旧部等广泛宣传蒋介石卖国,命令张学良不抵抗,动员他们起来抗日。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走了大半个东北,历尽艰辛。当时,我虽然-还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学生,但讲抗日救国这一套,还确有一股子虎劲。我常说:“东北人民应当有志气,自己武装起来抗日,蒋介石是靠不住的。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出卖东北,我们要自己组织起来收复失地。”我们组织义勇军是从皮口、庄河、安东、通化、宽甸、桓仁教育界开始的。记得我和同行的老李(回族)一起,在他的老家通化过的照历年。那时正是隆冬季节,我们顶风留雪日夜兼程。去宽甸的那天,朔风怒吼,拂晓的寒气砭人肌骨。当走进被称为宽的“摩天龄”时,好心的车老板对我们说:“你们先下来走吧,我赶空车过去,免得出事。”我们下了车,挪动着麻木地双脚仔细一看,只见被冰封雪冻的山坡像镜子一样光滑。山脚下还有一条很深的沟,如果稍一不慎滑下去,可能就“呜呼哀哉”了。我们蹑手蹑脚地在山岗的漫坡上移动着,到了比较陡峭的一段,简直无法立足,只得小心翼翼地爬了过去。从宽甸到桓仁路过的高山峻岭,一上一下就有六十里地。山岭上的路坎坷不平。有时我们以步当车,边走带爬。在辽源,我们通过熟人串联了二十几个积极反日的青年骨干开会。这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听了我们介绍沈阳失守的经过及蒋介石现在还顽固地执行不抵抗政策后,怒不可遏,撸胳膊绾袖子地说:“他们不抵抗,咱们自己抗!”就这样,通过串连很快地就组成了抗日义勇军,队伍浩浩荡荡,曾一度攻打过四平。当时,西丰县的县太爷姓冯,是车向忱老师的老相识,沈阳两级师范毕业生。车向忱老师向他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我们走后,他积极组织保安队,用土枪土炮打日本。我们经过四平到哈尔滨东的苇沙河邢占清旅的一个团,动员他们起来抗日。我们向全团官兵说:“你们要抗日,'”大我们给你们做宣传:你们缺军饷,我们给你们募款……。大地激发了官兵们的爱国热情。我们的工作没有白做,这支队伍在邢占清的领导下,终于走上了抗日的道路。我们返回哈尔滨后,相继又奔赴齐齐哈尔工作。那里的教育厅长姓郑,他的孩子和我们有同学关系。就这样通过同学找同学,先后串联了十几个人,很快就造成了一点声势。正在准备对敌开展工作的时候,由于形势所迫,我不得不离开齐齐哈尔去哈尔滨。在我返哈的途中,正巧遇上车向忱老师也回哈尔滨。火车上我们谈到搞义勇军的事。我说:“东满、南满、北满都走遍了,到义勇军中也活动了,但都没有成功。看来搞义勇军非自己搞不行了。”于是,在哈尔滨我们自己开办了一个中医院,院长姓关,是东北特区法院的一位法官,他积极主张抗日。副院长由车向忱老师担任。还有曾和我一道去邢占清旅宣传抗日的那位吕医生。吕因为在济南领导抗日斗争被通缉,是隐姓埋名来东北抗日的。此外,车向忱老师还筹办开了一个鞋铺做掩护。我们就是利用医院、鞋铺作为开展抗日活动的据点、联络点。不久又根据形势的需要,车向忱老师在辽宁教育界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很多人都认识他,容易暴露目标。为了工作方便,为了更加广泛地发动群众武装抗日,经商定车向忱老师仍留在北满以哈尔滨为活动基地;我去南满:小李在通化八道江他的家乡一带抗日。时间在一九三二年三月,我们分手。车向忱老师去黑河给马占山送委任状;我到沈阳找张金辉等东大的同学组织抗日义勇军,坚持武装抗日。 四、活跃在辽西战场上 在我没到沈阳之前,张金辉等人已经和张学良办的学兵队的戴昊、东北讲武堂的范甫忱,当过土匪的吴海山等组织起抗日义勇军,轰轰烈烈地干起来了。他们曾指挥抗日义勇军袭击沈阳飞机场。到沈阳之后,我与张金辉、郭明德等人研究决定分散活动,在清原、铁岭、开原、法库一带组织义勇军,打击敌人。我负责到新民一带义勇军中去工作。兜里是分文皆无,在谁家住就在谁家吃。当年抗日救国的工作条件实在太艰苦了。没有活动经费什么事情都不好办。我考虑不能只在城里活动,于是通过人介绍去农村联络抗日民团,组织保安队。不久,我和张金辉去北京,到抗日救国会筹集活动经费。找到了高崇民和阎宝航,向他们陈述了我们开展武装抗日活动缺乏经费的困难情况。他们同意由“救国会”拨给我们一笔款。我携带这笔活动经费返回辽宁的新民县。从一九三二年春到一九三四年春,我一直在辽西一带组织抗日义勇军。辽西新民县抗日义勇军的成分很复杂,其中包括民团、绿林军。虽然人数众多,但不是你下命令他们就听的,组织起来很困难。一九三二年五月,戴昊、江涛、那拯彬和我到辽西一带开展武装抗日工作。经过努力,我们逐渐把辽西地区分散的抗日力量组织在一起,成立了“东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共计八百多人,有几百支枪。总指挥是我,江涛任参谋长,军事负责人有戴昊、那拯彬等人。总指挥部设在新民县东二十几里的长沟沿—地方保安队骑兵分队李队长办公的地方。李队长是个地方的开明绅士,同情抗日。我们为了争取他抗日,经过一位姓李的回民老乡介绍认识了这位李队长。记得我们第一次相见是在他的队部办公室里。他果决地表态说:意抗日:”我们委任他做抗日义勇军的营长并通过他又结识了长沟沿另一个地方保安队姓吴的小队长,他没少给我们通风报“我愿信,在战斗中起了不小的作用。有一次,吴小队长接到他们上司通知,让他们立即配合日军在长沟沿一带围剿、追击抗日义勇军。他马上告诉了我们,使我们有了准备,没等日军到来我们已经钻进高粱地里,敌人扑了个空。我们抗日义勇军的队伍驻在新民县的三角地带。一次,有四五十个日本兵去新民经过我们这里,我们只有十几个人想打伏击干掉他们。这时正是·深秋,寒气逼人。我们没有穿棉衣,踏过冰冷的河水,隐蔽在青纱帐里。新民县农村种高粱的地带较多,便于藏身。我们是想等日军过河再打。结果由于我们失去了战机,伏击没打成,反倒使日军到我们的驻地进行搜查,逼老百姓交出义勇军。老百姓恨透了日本鬼子兵,他们宁死不说,从面保护了我们的安全。我们经常化整为零,打扮成老百姓,除了平时伺机乘虚零打碎敲地打击敌人之外,活动比较频繁的是破坏铁路交通。住在巨流河铁道边上有个姓孙的铁路工人(名字记不住了),为了打击骄横残暴的日本侵略者,他组织了二、三十人的铁路破坏队,专门破坏铁路。在对敌斗争实践中使我们逐渐认识到,抗日义勇军应该以工人、农民群众为基本骨干。所以我们很重视这支铁路工人抗日队伍。以他们为主体组成的铁路爆破队,成了我们“东北义勇军总指挥部”领导下的抗日尖兵。戴昊、那拯彬、金硬等一些军事指挥人员经常组织人力,利用敌人打出的但没炸响的炮弹,趁夜深人静时,用以去爆破敌人的铁路和桥梁,破坏敌人的铁路运输,使敌人列车停运事件屡屡发生。为了教训日本侵略军,我们指挥部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决定攻打新民。日本驻军在县城,周围设有电网。为了扫清攻城障碍,我事先潜入新民县城里了解情况,有时到一位积极抗日的阿所在的清真寺落脚,有时住在一位姓张的小学教师家里,做准备工作。通过这位小学教师我们与新民县电业局取得了联系,并同电业局工人商量好,要求他们上半夜送电,下半夜不要送电,以便于我们夜袭。为了阻止敌人增援,决定在仗打响后即把通往巨流河的桥用火车头堵住;我们还调来力量较强的第四民团守在铁路沿线,专门对付日军的铁甲车。这次由我任总指挥,组织三路人马,攻打新民。那时我刚二十岁出点头,没有指挥经验。义勇军的成分又很复杂,平时缺乏训练,行动迟缓。那天本来计划夜袭,但等各路队伍赶到城门时,天已大亮了,结果我们没能打进新民城里。但这次军事行动政治影响很大。后来据传,城里的敌人得知我们围城的消息,吓得魂不附体,慌作一团,日本兵争先恐后地往装甲车里钻;日本浪人把木展(拖鞋)跑掉,东一只、西一只甩在大街上。攻城计划未遂,日伪军反击。我们分路撤退。江涛等率领一支队伍撒到秀水河子。敌人追到那里,我们搞来一门敌人的大炮,利用这门炮助战,打死日军二十多人。日军为了报复,派兵到处围剿。可是抗日义勇军把枪一插就是普通老百姓。敌人找不到我们的队伍,只好东一头、西一头地乱搜、乱捕。抗日义勇军中队长吴海山,曾当过土匪的头,报号“老头好”,大家都把他看作是一个爽快的好老头,颇有威望。吴海山此时混迹于群众之中,被捕时是个普通群众的打扮。江涛穿的也是老百姓衣服,被敌人捕后也没抓住任何证据。在群众的掩护下,他二人都作为“良民”被保释了出来。秀水河子一战打出了我们的威风,远近驰名。老百姓赞扬义勇军作战英勇,受伤不叫苦。这次日军受到一次教训,丢了大炮又死了人,又气又恼。于是,又搞了一次报复性的大扫荡,三番五次地搜查,最后把被我们缴获的那门炮从草垛里找到才算了事。他们放火烧了老百姓的房屋,屠杀一些无辜的百姓,也被烧成灰烬。“老头好”家的房屋 五、二次策反 工作在新民县城的第二年,为了更好地开展抗日工作,在南满活动的张金辉、戴昊、郭明德、江涛和我,于一九三三年组成“中华青年抗日铁血团”;从北平来的李士廉也成了我们“铁血团”的主要成员。他原是东北军独立步兵第二旅的参谋,“九·一八”事变时在东北讲武堂学习。“九·一八”事变,讲武堂解散后,他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在开原、西丰一带活动。一九三二年初,他跟方文图组织了“东北抗日义勇军”,曾在沈阳袭击过东北兵工厂和大北关警察署,随后在辽中、黑山县一带打击敌人。这年秋天,李士廉去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经过在“救国会”工作的老乡、同学张希尧介绍,回沈与张金辉接上了关系。一九三三年三月份,我们在沈阳大西门的一家小客店见了面。后来他参加了我们的铁血团。我们派他去伪安国军步兵第二旅做策反工作。行前,我们分析了安国军步二旅的情况:该旅副官长肖钟英是张金辉的老相识,此人年轻,有正义感,积极主张抗日;而旅长苏正格又与肖有亲属关系。肖钟英和他们的参谋处长都是东北讲武堂毕业的,李士廉又是东北讲武堂最后一期学员,原来就是军官,派他去做这个策反工作比较合适。李士廉在张金辉收到肖钟英的回信后,即化名李应势欣然前往吉林太平川。在肖钟英的引荐下,李士廉在通辽见了旅长苏正格。经过考试,参谋处委任他为安国军步兵第二旅少校参谋。他利用伪军官的身份作掩护,谨慎地在伪军中宣传反满抗日的思想。李士廉所在的安国军第二旅开到开鲁后,不久继续向热河挺进。在行军途中,李士廉发现曾当过土匪(匪号“中华”)的第二团团长企图叛变,及时把这个情况报告了肖钟英,采取紧急措施,“中华”的叛变阴谋未能得逞。第二天,途中又遇到张海鹏的儿子拉起的一支队伍拦路。肖钟英派李士廉去谈判,达成了互不相扰的协议。通过这两件事,肖钟英更加器重李士靡,策反工作很有希望。但后来由于特务告密,亲日的苏正格突然逮捕了参与策反工作的肖钟英,并将他杀害了。李士廉见势不妙,趁新来的武副旅长招兵买马心切之隙,要求去辽西“扩充队伍”,借机离开了安国军步二旅,回到沈阳。此外,我们在沈阳的伪靖安军中也做过策反工作。在我们的抗日宣传的影响下,伪军中的一些“红袖头”(即靖安军)对日军的侵略和“满洲国”的法西斯统治日益不满,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帮助抗日,不仅给我们通报消息,有时他们还在行军中故意往路边掉子弹,以便义勇军随后去检。我们除在伪军中搞策反工作外,还印刷抗日宣传材料,成通过邮局寄,或暗中投放到机关、学校、医院等单位的收发室,有时还把它投到白、美、英、俄等领事馆门前的信箱里。我们有时还通过贴标语,撤传单,破坏“满洲国”的社会秩序,以打击敌人气焰,鼓舞人民的斗志。 六、“太平世界”不太平 盛夏和初秋季节,我们利用青纱帐起,到农村组织义勇军,用真枪实弹打击敌人。到冬天,我们就进城组织城市人民进行反日斗争。在城里向工人、市民宣传抗日救国,组织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与日伪作斗争。如砸大烟馆、炸火车站、袭击领事馆、扰乱社会秩序等,闹得敌人一夕数惊,惶惶不安,以戳穿敌人所谓的“王道乐土”、“安居乐业”、“太平世界”的欺骗和谎言。我们在城市的抗日活动,得到各阶层人民的支持,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日伪军警跟踪追击,到处搜捕我们,可是一直没抓住过我们。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开会,敌人来搜捕。江涛等人被捕,群众却把他们当“良民”保了出来。在日伪统治下的沈阳,被一片白色恐怖气氛所笼罩。日本帝国主义除了用残酷的法西斯手段统治外,还实施罪恶的“纵毒祸华”政策,用毒品腐蚀、摧残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大烟为了馆遍设全城,不少年轻人也进去“喷云吐雾”。给毒害中国人民的日本侵略者以惩罚,我们决定炸大烟馆。用的是自制的土炸弹;制造土炸弹还是我在北平学会的。一九三二年底,撤离新民后,我专程去北平打算找那些思想先进、积极抗日的老同学,请教他们怎样抗日才能卓有成效。此行两月有余,颇有收获。在东大(“九·一八”事变后,迁到北平)积极抗日的郑鸿轩同学(中共地下党员),提醒我说:“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那么积极,为什么不参加‘反帝大同盟’?”经他介绍,我知道这个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外围组织,是坚决抗日的团体。于是我欣然参加了。在北平,我曾去西山卧佛寺看望张希尧同学。他和阀宝航、宁匡烈等人正在办“西山训练班”。我在那里跟着学了一点马列主义、游击战术和爆破技术。配制炸药就是跟宁匡烈(东北大学化学系学生)学的。在沈阳我们去炸大烟馆,有张金辉和我;还有另外两三个人,携带好自制的土炸弹,都扮作抽大烟的,陆续到了大西门里的一家烟馆。迈进门槛,刺鼻的鸦片烟味扑面而来。我四面环顾,只见屋里烟雾缭绕,床榻上都摆着烟具,有的是一个人躺在鬼火似的烟灯旁贪婪地在吱吱猛吸;有的则是二人对抽。我们各自找好位置,躺下慢腾腾地装作烧烟泡,趁人不注意时便把暖水瓶(土制炸弹)盖上的引线点燃放在床下,从容不迫地吸完烟,结了账,大模大样地离开了险地。时间不长,只听轰地一声,我们放的定时炸弹爆炸了。虽然它只是炸毁烟馆一些家具,炸掉了几个“烟鬼”的胳膊腿,但却轰动一时,在政治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消息不胫而走,人们奔走相告,越传越神奇。说什么:“义勇军真了不得,他们进城把大烟馆都给炸飞了!”敌人气势汹汹,吼叫“立案追查”,还举行什么记者招待会“说明情况”,一时闹得满城乌烟瘴气。我们四处出击,越干劲越足。街头巷尾不时出现我们贴的反日标语、抗日宣传材料,敌人越禁止,我们印发的越多。一次,我们又决定炸南满火车站(即现在的沈阳站)。沈阳车站,历来是四通八达的铁路交通枢纽,当时的客货流量也是相当可观的。虽然旅客中有日本人,但主要的还是中国的老百姓。如果炸火车站,怎么才能做到既在政治上给敌人造成影响,又不致伤害自己的骨肉同胞,为此我们颇费脑筋。曾多次去南站观察地形,经反复讨论,最后才决定了定时炸弹安放的位置。一天,南满火车站候车室的内外,依然是人群熙熙攘攘,突然只听“砰”地一声巨响,人们大惊失色。坐在候车室长椅上的老爷、阔少象弹簧似的腾地跳了起来,惊慌失措;众多的旅客们大呼小叫,人声鼎沸。驻车站的日本宪兵自然是手忙脚乱了一阵。当普通的中国老百姓一阵惊悸过后,明白了事实的底口蕴,无不暗自高兴,悄悄地私下议论:“准是抗日义勇军炸的,干的真漂亮!”随着南行北往的列车,这个新闻被带到了祖国的四面八方。继炸南满火车站成功之后,我们又决定于一起对敌人震动大的事件,让全世界人们都知道中国人决不甘心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任人凌辱,他们正在战斗。我们决定爆炸沈阳各国驻“满洲国”的使馆,让一些外国人也知道点中国人的厉害。由于配制炸药的药物缺乏,所以这次配制的是杀伤力较小的黑色炸药。我们这次主要爆炸目标是日本领事馆,其他驻沈阳的外国使馆我们也都放置了土炸弹,但结果爆炸的是少数,仅仅崩坏了…些房屋的边角,没伤着人。但我们这一行动却碰到了日本当局最敏感的那根政治神经。凶残的日本侵略者,暴跳如雷,遍撒罗网,杀气腾腾地开始了野蛮、空前的大搜捕。我们最先被捕的是郭明德和江涛同学。他俩的公开身份是《满洲日报》的记者。为了掩护抗日活动,他们都在沈阳安了家。他们的家是我和张金辉经常落脚的地方。因为他们在沈阳有固定的职业和家庭住址,目标大而明显,因此敌人比较容易地逮捕了他们。相继,为我们提供印刷地点的张姓同学父子以及我们的联络员—―沈阳大北关的铁匠铺掌柜等许多抗日积极分子,也被捕了。与此同时,开原、西丰等我们在南满的抗日据点,也有许多人被捕,甚至惨遭杀害。为了避免此事波及到北满,当张金辉得知郭明德被捕的消息后,他立即派他爱人到客店找到李士廉让其转告我,并让我火速去哈尔滨给车向忱老师送信,告诉他们迅即撤离。我得到李士廉的通知,随即启程去哈尔滨报信。记得在北满我们进行抗日活动时,有一次日本人在哈尔滨市举行什么庆祝“太平”的龙灯晚会。我们决定搞一次活动,闹它个“不太平”,当时由于炸药不好弄,我们便买了些鞭炮。在大街入多处,把高升炮横着放,闹得游人乱了套;把摔炮捆在一起,往公共厕所里一摔,炸得粪尿腾空四溅,吓得厕所里的人和四周人等惊恐万状。我们也随着人群乱喊‘谁炸的’日伪军警赶来现场,谁也没抓到,把敌人举办的这个庆“太平”的龙灯晚会,搅个一塌糊涂。 六、向国联调查团上书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铁蹄所到之处,攻城略地,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在中国人面前犯下了累累罪行。可是,日本帝国主义却向国际联盟捏造种种谎言,欺骗世界舆论,为其侵略行径诡辩。他们胡说:(一)东北四省不是中国领土:(二)“九·一八”事变是一偶然发生的事件;(三)日本侵占沈阳是由于中国军队破坏了南满铁路,日本是自卫战争;(四)日本侵占东北各城市是因为中国政府不能担保东北日侨的生命财产安全;(五)满洲国的建立完全出于东北居民的自愿,是东北居民自治运动的结果,等等。而面对敌人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的是蒋介石,他出卖了东北,后来又以“诉诸国联”为口实,继续坚持推行其不抵抗政策。当时国联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最初是隔岸观火。当英、美帝国主义发现日本企图独霸中国,有可能危害他们各自在华利益时,才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在国联理事会上通过决议,派“国联调查团”赴中国东北调查。一九三二年春天,“国联调查团”来中国的消息在报纸上登出和在电台广播后,沈阳各界爱国人士冒着生命危险,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材料,想方设法递交给“国联调查团”,以揭穿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所捏造的种种谎言。李顿调查团在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抵沈阳。据记载,仅四月下旬国联调查团就在沈阳接到二千多封中国各阶层人民揭露、控告日本侵略者的信件。我们是东北救国会派来东北在沈阳做地下工作的。我到沈阳时,张金辉等正忙于准备向“国联调查团”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罪行。因此,我立即跟张金辉、战××、江涛、戴昊、李士廉、那拯彬、郭明德等八人一起,在沈阳、铁岭、开原等地奔走,发动学生、工人、农民、职员、医生、商人等写揭发控告信,寄给英国驻沈阳领事馆转“国联调查团”闭长----英国的李顿爵士,或直接寄到调查团在沈阳的驻地—-沈阳大和族馆(今辽宁宾馆)。我们把搜集好的材料,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千方百计地交到驻沈阳的英国领事馆、英国教会学校和英国医院,由他们代交“国联调查团”。我们的信件,有的是用学生名义、有的以老百姓名义,还有的是用某医生的名义,把信件译成英文,以·多种形式巧妙地转交给“国联调查团”。我们抗日救国会地下工作小组的八个人,是和沈阳青年会小组的巩天民取得联系。巩天民是开设边业银行的银行家。我平时常到边业银行或巩天民家借进步书籍看,他还经常在书中夹上宣传抗日的材料给我。这时,我经常借助传递书籍之机把搜集整理好的材料夹在书里交给他。然后,他通过刘仲明与小河沿施医院院长雍大夫接合,再由雍大夫引荐通过倪博士,以宴请李顿团长的方式,把材料最后送到“国联调查团”的手里。由于日本警察的严密监视,李顿调查团全体人员不能在调查团驻地大和旅馆审阅我们递交的材料,而要到沈阳的英国领事馆去审阅。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是一九三二年十月二日发表的。英美帝国主义为了达到其共管中国的政治目的,在公诸于世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里,极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尽管如此,他们也无法全部掩盖事实真相,对于中国人民的正义呼声,不得不有所反映。例如《报告书》中这样写道:“收到信息为农民、小职工、城市工人及学生所投寄者……在此一千五百件之书信,除两件外,均对满洲国政府及日人深表仇视。此种信件皆甚诚恳并足为民意之表现。细心研究各方所获得之证据,无论公私谈话或书信文件,吾人的一结论:即一般中国人对‘满洲国’政府者,在当地中国人心目中,只是日人之具而已”。《报告书》中被迫承认的事实可归纳如下几点:(一)东三省是中国的领土;(二)“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有计划发动的;的行为;(三)“九·一八”事变中,日军的军事行动不是自卫(四)伪“满洲国”是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不代表东北人民的民意。这一切正是中国人民,首先是沈阳各阶层爱国人士向国联控告日本侵略罪行所取得的胜利成果。一九三三年二月由于多种因素促成的国际联盟大会通过决议:不承认“满洲国”。致使日本帝国主义恼羞成怒,他不但宣布退出国联,还按图索骥,按照《报告书》中提到的写信的人或提供证据的人的职业线索,疯狂地进行追查。他们终于找到蛛丝马迹,并张开罗网,大肆搜捕。一九三三年冬,敌人加紧跟踪追索,在一个夜晚捕去了沈阳同仁医院院长刘仲宜大夫,在逮捕刘仲宜大夫时,还搜查出一台油印机和一些抗日宣传品。这台油印机是我们寄存的。平时,我们在一位姓张的同学家油印抗日宣传材料,待我们出城时,为了防止意外,便把油印机送到英国势力较强的同仁医院,请爱国医生代为保存。有一天,张金辉和我用手提包装妥油印机到同仁医院找到张火“我们有件东西想请您代为保存。”他听我们一夫,对他说:说,根本没有问我们寄存的是什么,便慨然应允。我们顺于耶把东西放在柜台顶上,随后跟同仁医院院长刘仲宜打了招呼。告诉他,我们把油印机存放在张大夫那里了。现在被人发现,他们从钢板腊痕上查出有与标语上相同的字迹。院长刘仲宜和张大夫等许多人都被捕了1尽管刘仲宜一再说明这油印机是患者寄存的东西,但敌人怎肯相信?刘仲宜被直接押送日本宪兵队。敌人随后即按病志上的姓名和张大夫讲的患者的脸型、身材胖瘦等在市内外到处遵查油印机的存放者。敌人岂知,我们到张大夫那里“看病”用的都是化名,而且息的是“胃病”、“感冒”普通常见病,敌人凭着真伪杂糅的容貌线索,在人海里空忙了一场。我们当时四处奔走探听消息,营救被捕的同志。因为刘仲宜大夫是英国学校毕业的学生,又信仰基督教,英国人把他保了出来。经多方营救,被捕的同志先后全部获释。但刘仲宜大夫因受半年多的酷刑而被折磨得精神有些失常,后来他到了解放区,当过医院的院长。我和张金辉在沈阳安排了栖性和被捕战友的家属。一九三四年回到北平,我们一起在东北大学复了学。原同班的同学都已毕业了。我只好由经济系转入政治系,以插班生进入二年级学习。那时为了抗日救国大业,就是抛头颅洒热血都心甘情愿。从此,结束了我在东北二、三年组织抗日义勇军和地下工作的一段抗日斗争生活;结束了我自发抗日的历史,开始了有组织地进行革命斗争的新阶段。 七、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开始新的革命征程 前边说过,一九三一年底我奉“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之命,从北平回到哈尔滨做地下工作,组织义剪军。当时我还不是共产党员,可是我在北平阅读过一些进步书籍,觉得共产主义有道理。在平时言论或辩论时,就表露点马列观点,因此,很多人都误认为我是共产党员。在哈尔滨做地下工作时期,“救国会”派来的人各党各派都有,青年党几个人怀疑我是共产党。他们封锁不让我知道内部消息;还设法不让我和车向忱老师接近,为此我决心和青年党决裂。由哈尔滨回到沈阳,我公开表示退出青年党(参加青年党共三个月)。一九三四年回到北平,我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任东北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负责领导学生的救亡运动。从此,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国难当头,在抗日民族斗争中使我从民族觉醒逐步提高到阶级觉悟,由爱国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这是那个时代进步青年走过来的一条共同的人生道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我和流亡关内的东北一大批人士一道组织各种抗日团体,继续坚持抗日复七斗争。抗日群众团体“东北民众救济会”下面设有救济院,制鞋用以解决流亡关内的东北人民的生活困难。这个团体一直坚持到“七。七”事“东北民众救亡会”,是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在西安事变立的。主要发起人有刘澜波、孙铭九、洪航、应德田、车向忱、韩士英和我等人。东北军青年军官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是该会的理事。“东救会”是围绕着“西安事变”搞起来的,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就结束了。最后一个救亡团体就是“东北救亡总会”。它是在“西安事变”后,由刘澜波、阎宝航、车向忱、李延禄、高崇民、谢放、苗波然、于毅夫、张希尧、栗又文和我等几十人发起,于一九三七年六月正式成立的,东北的名流几乎都参加了。目的是统一东北各流亡团体的抗日力趾,总会设在北京。上海、西安等地设有分会。它一直坚持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在“九·一八”事变后二、三年的岁月里,遍地开花的东北义勇军,曾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终由于众寡悬殊,尤其是因为没有正确的领导,因此,先后失败。经过大浪淘沙,这些抗日武装中的精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都成为抗日的中坚力量。这其中有不少人加入了一九三四年秋中国共产党开始组织和统--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转战白山黑水之间,和东北人民一起为抗辑战争和民族解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回顾这段历史,灾难深重的东北人民从切身体验中懂得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一切胜利的根本保证。 |
上一篇:国民党116师师长刘润川被俘后见闻下一篇:“九·一八”事变前后亲历记